虚拟网络空间形成的真实社群,在城市生活中的意义越发显明。2018年底,澎湃新闻的首个研究项目“网民20年:互联网社群研究”,正是由此展开。以下是项目成果之一。
这里有关乡村教育的不少背景情节,都可与上篇呼应。上篇说到,高三生自发形成在线教育社群,尤其是小镇上的那些少男少女,这是他们为了求学之路而自救的方式。而那些走到了其他路上的朋友们,也能在网络上找到组织,获得一种谋生方式。网红三炮的团队就是如此。
欧可可像刺猬躲在羽绒服毛领围成的壳里:“我不会。你呢?”对方抱臂冷笑:“正经人谁会拍段子啊!”

随后,欧可可用手指撑起嘴角,对着镜子挤出有名无实的微笑。字幕是内心独白:“是啊,谁会把生活拍成段子啊,谁都想活成段子里的自己。”
这个视频像是表明心志。欧可可前一晚直播时哭了,她不愿讲出原因。也许,这个日子放大了她对屏幕内外的矛盾人生的怅然。但视频没能引起粉丝共情,评论只是“生日快乐”的机械接龙。
快手笑匠们将“段子”和“生活”隔离。为了逗你开心,他们设计情节、道具、人物关系,遮蔽真实自我。但那些无厘头的剧情、夸张的造型和道具、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能在生活中找到注脚。
我决定写一个连通屏幕内外的故事。它是三炮的故事,也是隐在“三炮”这一网名背后的孟焕实实在在的人生。
广西上林县塘红乡的三炮团队是最受媒体青睐的快手网红之一。他们以《叛逆少年》系列短剧风靡快手。三炮、表锅、疼叔、蓝城、大表哥、小马林、阿蓝、大卫等八人是核心角色。他们自称塘红F8。后来团队加入了新成员,欧可可是其中之一。

2019年1月6日,通往广西上林县塘红乡的县道一侧。本文照片除特别说明外 均为周平浪 摄
两三年前,塘红F8的很多视频,是在田埂上打架,在水田里打滚。对满脸是泥的F8来说,这并非对当时快手流行的“狠活”简单跟风,而是自己童年时在田地里发明的纯真游戏。
1996年,北京中关村带领中国人走向信息高速公路。和诸多这一年前后出生的小镇孩子一样,表锅、蓝城、大表哥、三炮与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个十年并无交错。
他们对互联网的最初接触,是小学时偷拿家里固定电话充Q币,是扮成黑色系的QQ空间,是爬墙逃学去网吧。
初中是转折点。原因就是“没有前途”。因为,学与不学,最后绝大多数人都要外出打工。
他们在小学还是品学兼优拿奖状的好孩子。上了初中,却很快成了叛逆少年。塘红乡唯一的初中,实行封闭式管理。表锅会翻墙跑出去上网。而大表哥跟学校请假,跑去网吧打游戏,半夜偷溜回自己房间,用被子把自己蒙在床的角落,大半边床空着,看起来没人。父亲第二天出门工作,他爬起来去网吧,度过新的一天。
他们成了自己口中的“坏学生”。“坏事都干尽”,也不过是旷课、逃学、上网、抽烟、喝酒、打架。

这里几乎没有“好学生”。不断有人辍学。初一有5个班,初二只剩3个。初一时一个班的四五十人中,能撑到毕业的不超过十个。
三炮扮演老师,在黑板前专心教学。学生歪斜着坐在板凳上,许多人已低头睡去。疼叔与小马林嬉戏打闹,疼叔拿起拖鞋向小马林拍去。老师转过身来吼道:“你们读书为了什么?”小马林百无聊赖地回答:“为了不让你们下岗!”“小马林,滚出去!”老师挥舞起教棍,大喝一声。视频戛然而止。
表锅、大表哥、蓝城、三炮,离开了家乡的学校。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开始了都市历险。
独自外出打工,表锅体会到的苦远超读书。身无分文的他,常常露宿天桥。但他不愿像父辈那样,1天14小时4万次重复同一个动作,更无法活在班组长的颐指气使之下。他频繁跳槽,有时三天就换厂,甩一句“我不干了”就走人,一分钱报酬也拿不到。最后,他不得不跟着一位塘红的模具师傅到东莞学习模具技术。
而蓝城去了老爸在佛山开的厂——天城五金厂——后来的视频中,蓝城饰演的酱爆的工作地。不过,蓝城在自家工厂没呆多久,为了获得自由,他很快加入跳槽大军。有一家工厂的老板很看重蓝城的表现。但女朋友被工友欺负,暴揍工友一顿后,他就潇洒离开了。
大表哥成了冲压机操作员。2019年1月7日,广西上林县塘红乡,三炮团队在拍摄段子。这种工作简单,却深藏风险,每天要像机器般重复固定动作成千上万次,稍不留神就可能断指伤残。有一次,大表哥动作稍微慢了几秒,裂了半个指甲盖。

曾经有人调侃,珠三角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接断指技术。这里每年至少发生断指事故30,000件,被切断的手指超过40,000根。
《叛逆少年》第八章《史上最强杀马特之劲爆尬舞大会》中,头戴大红色假发的大表哥,在漫天纷飞的水泥中挥舞着铁链,教两位懵懂的表弟跳“吸引异性的舞蹈”。蓝城饰演的酱爆从树林中跳了出来:“我酱爆好中意你的舞步,在捏个moment,我酱爆感觉到,我要爆呃!”他头戴紫色假发,身着蓝色西装上衣,举起右手,竖起了大拇指、食指和小拇指。
“天城五金厂,三号车间,五百八十吨冲压机操作员,酱爆呃。”蓝城用三根手指,从上衣口袋中夹出手机,打开闪光灯,一场斗舞一触即发。


如蓝城所说,他确实来自天城五金厂,曾是冲压机操作员。被忽略的是冲压机与三支竖起手指的关系——或者说,是与那两根消失的手指的关系。三炮直播时,揭秘了这个他设计的手势。很多人以为是“rock you”,但在后面的情节里,即便拿手机,蓝城也只用三根手指。经历过的人一眼就能分辨,那是断指。

工厂的工作繁重空洞,将人当成机器。频繁跳槽不过是发泄的出口,飙车才能赋予生活更多激情。
2015年,三炮、蓝城、小马林在佛山相聚,组织起一支车队,成员来自广东、广西、贵州、湖南各地。
一起飙过车的是真兄弟。只要存够钱,首先要买的一定是摩托车。“你可以不认识我,但一定要认识我的车。”他们的车各有自己的标志——绿色轮子、紫色车把,或夸张的贴图。这可以让他们在本地人面前抬起头。
这一年,快手从GIF动图工具转型成短视频社区。蓝城和三炮常在快手上发布一些飙车片段。蓝城慢慢积累了八九千粉丝,三炮则有两万多。

2016年春节过后,三炮、蓝城、小马林留在塘红拍快手。又过了三个月,表锅决定逃离令人筋疲力尽的模具厂。而疼叔因修车匠身份,被谈了三年的女朋友抛弃。靠打工积攒资本开厂的梦想遥不可及,他们一时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就在这时,三炮召唤他们回塘红。
塘红公路车辆稀少,飙车条件得天独厚。在夕阳下,在大雨中,车队在大山间呼啸穿梭。
三炮团队的视频一度在当地带起飙车风潮。提起三炮,人们都知道,“是玩翘头的”。有人羡慕他们的车技,有人学着改造摩托。塘红有几个小学生飙车身亡,大家觉得他们是模仿三炮。当地派出所为此专程上门警告。快手官方也常以违背“传播规范和伦理”为由,封禁他们的作品。
在那之后,他们会在飙车镜头上加字幕:“镜头经过加速处理,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叛逆少年们过去不吝于仗义出手,潇洒辞工,恣意飙车。但现在,他们不得不担心,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言行会“带坏小孩”。
叛逆变得需要审核,需要挑选。有时还需要隐藏。很快,飙车镜头从他们的作品中消失。
他们仍会每天飞驰数百公里去县城的酒吧、宵夜店,仍会在雨中驱车狂飙,每隔两三天便收到一则交通违规通知。但这些都只发生在午夜。白天,那辆黑色大黄蜂跑车静静停在三炮家的三层小楼下。

三炮的交通工具再也不是摩托。甚至,作为道具的摩托,也很少在他的作品中出现。
那辆“鬼火摩托”还是不时出场。它加装了4层尾翼,使车身高出近1米。每层尾翼下加带一个夸张的“车牌”。8根炫彩的排气管,朝四面八方伸展。挂满彩灯后,对外行来说,它就是名副其实的“鬼火”(鬼火是一款摩托车型,因适合改装备受飙车爱好者青睐,成为改装车代名词)。

真正的飙车党知道,要想做出更高难度的飙车动作,车越轻便越好,最好卸了车头。即便通过加装排气管使奔驰声更响,排气管也不该朝上,那样只会阻碍摩托飞驰。
“鬼火摩托”不只是博人眼球的道具,还暗藏着飙车群体内部的鄙视链——这是千锤百炼的技术派,对金玉其外、车技一般的器材党的反向讽刺。 很难说街头的围观者和网上的数百万粉丝能领会这层真意。当三炮骑着“鬼火摩托”在上林县城的街头穿梭时,收获的是街边少女的阵阵尖叫。

三炮团队确实越来越在意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作品中飙车元素的消失是一个开始,媒体的介入让他们更加谨慎。
为了配合媒体拍摄片头,F8车队再次上路。他们以极低的速度慢腾腾前进。这是一次集体展演,而非昨日飙车风采的重现。
看到媒体的标题“打工是不可能的”,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经历,不是这句戏谑语的原创者“窃·格瓦拉”,而是担心会不会“带坏青少年”。疼叔说:“不打工也不是不行,难道所有的人都应该去打工吗?只是,网上的人怎么看我们……”
也许少年们会回想起在佛山仙湖、西樵山飙车的过往。那是他们叛逆无拘、自由随性的最后时光。
快手网红的生活重心也逐渐转移到晚上。最初,夜晚不睡是要做剪辑和后期。答应粉丝更新,三炮不愿食言。后来,大家都习惯了晚上看视频、找灵感、聊创意。

下午三四点起床后,团队成员陆续来到三炮家客厅,看有没有人要拍段子。事先没有计划和分工,要不要拍,怎么拍,和谁拍,都是看情况而定。
《叛逆少年》第十七章更新后,塘红下了两个月的雨。无法按照原计划拍摄第十八章,但团队成员的生活一如往昔。下午,大家还是集合,直播,打游戏,刷手机。到了午夜,一起烧烤,或驱车远赴县城。
一旦重复起来,自由的日子竟也变得和工厂的机器一般。三炮闭着眼睛却睡不着。这样的生活方式成了焦虑的症候。在直播间,三炮会戏谑地求老铁安排些助眠偏方给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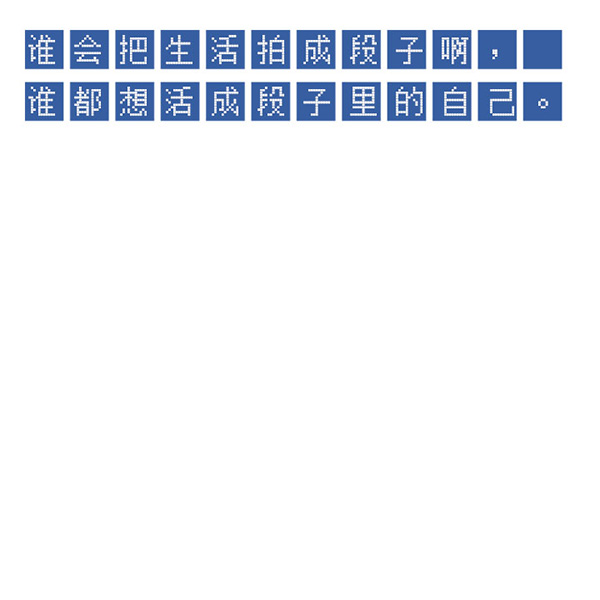
有一回,蓝城动员大家,出去与其他大主播走动,“蹭蹭粉”。他打点好一切准备出发,又被三炮叫住。三炮还是想打造“有灵魂的作品”。而后,他们打造了《叛逆少年》系列剧,涨粉无数,风靡快手。
但是,一茬又一茬快手网红在朝生暮死的互联网中挣扎出世,快手江湖后浪推前浪,一刻也不停歇。
窝在塘红山村里的网红们直言,自己已走到特别安逸、没有任何追求的状态,“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

焦虑是无孔不入的烟酒,填满年轻的愁肠。身心疲乏,创意枯竭,涨粉有限,收入下降,未来不确定。问题接踵而至。
疼叔看起来和“叛逆”不沾边。他很小就随父母在海南生活,初三才转回塘红。因安心读书,成为学校的异类。他希望升职高,但家里拮据。在随后的打工生涯里,疼叔一心学好手艺,打算自己开厂。
疼叔做快手的动机很简单:赚钱。《叛逆少年》中,每个人都有对标自己的角色。疼叔扮演的是勤恳朴素又有些木讷的老一辈人。
原先拍段子,赚的是广告费。现在,快手也做起直播——人气黄金期已过,广告收入下降,想把粉丝变现,直播几乎是必然路径。但疼叔总有“骗粉丝礼物”的感觉。即便已然又弹又唱,比其他直播散嗑、闲聊的主播投入更多心力,他内心仍旧背负道德压力,每天都在养家的生存要求和不劳而获的自责之间拉锯。
蓝城也陷在矛盾的焦虑中。他热爱嘻哈,会把自己的音乐作品发在快手上。收获的评论多是空洞的“666”,但他还是有了一些作品粉。可是,现阶段这样的作品不会给他带来收益,反而渐渐引来非议。有人说他飘了,没了农村人的样子。
“酱爆”太深入人心。人们无法接受,这个乡村痞子背后是一个爱嘻哈的酷男孩。蓝城学着单纯把快手看成赚钱渠道,放下自己的坚持和曾经的激情,追求“利益最大化”。
三炮在县里投资的以“野狼”为名的系列餐饮业,也入不敷出,危机深深。他终于同意,和大家一起搬去南宁,改变松散状态,组建运作更规范的公司。

短视频江湖在改变。关于快手青年的叙述,从此前的猎奇与贬低,慢慢转向底层经验、成功故事和找寻新出路之间的张力,呈现没落的“全村的希望”式悲情英雄。
我并非要说快手青年都很有主体性,也没有否认他们的赚钱动机或如今的“悲情”现状。只是想说,他们在努力过生活,有了“淘金”机会时,为了逃离工厂,年轻人就奔向快手。
人类的悲欢有相通处,生活里的种种挣扎也相像。至少,塘红的快手青年们,没有自视高/低人一等。表锅会好奇我们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三炮则跟我们开玩笑,说我们不碰烟、酒、游戏,生活了无乐趣。
快手青年常被当作既定剧本里的特定角色。“底层”、“土味”是其核心特征,用以反映主流文化的端正,或是资本游戏的荒诞。来塘红前,我也常在这些刻板印象间穿梭,不自觉用“魔幻”的滤镜理解他们。
但成了快手网红,并非就“走上人生巅峰”,或落入“残酷底层物语”。生而为人,他们与我们都会面对这些境遇选择,没有谁比谁更厉害或更悲情。
“我们都一样”,就是把快手青年看作普通群体,他们自有组织日常生活的方式。这不是要无视阶层和文化差异,也不是抽象疾呼人人平等,而是着眼于那些生活和情感的相通处,松动刻板的想象。
在三炮/孟焕的双面故事里,我最终想说的,也只是很平常的想法:快手青年要赚钱,也有视频以外的生活、道德和意义。快手青年中,有些玩乐在前,有些利益至上,有些有独立精神,有些则随波逐流,有些是以上特质的综合。
这用得着说吗?但人们常常不这么想。正如人类学启发我们的:有时,我们需要花很多力气和时间来倾听、记录,最后只是说出稀松平常却未必显而易见的事。

我是多家高校、众创空间的创业导师,关于企业融资、创新创业的问题,问我吧!
我是多家高校、众创空间的创业导师,关于企业融资、创新创业的问题,问我吧!
我是多家高校、众创空间的创业导师,关于企业融资、创新创业的问题,问我吧!
- 本文固定链接: http://douyinkuaishou.cc/?id=690
- 转载请注明: admin 于 抖音快手 发表
《本文》有 0 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