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日前发布了一封名为《胡鑫宇,请给心理指导师五分钟》的信,引发了大量质疑,并迅速登上热搜,有网友称其为“一场盛大的PUA”。
类似的心理疏导话语在中国并不少见,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张鹂在Anxious China一书中研究了当下中国兴起的“心理咨询热”。她发现,心理咨询自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后,发生了许多具有本土特色的改变,无论是“积极心理学”被突出强调,还是不同文化语料库的杂糅混搭,《易经》、沙盘治疗与催眠都成了热门元素。
心理学也发展出了人员和组织管理功能——《胡鑫宇,请给心理指导师五分钟》的作者是张青之,职业头衔为“社会心理指导师”,有知乎网友提到,这是一个区别于“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的职业,目前只在北京市存在,面向的对象主要为“社区、党务、机关和学校等人员”。
还有许多人担心,心理治疗文化中对自我决定与自我管理的强调,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结构问题转移到个人心灵上。
当下是不是正发生着一场“心理热”?看心理咨询的年轻人是否越来越多,心理文化是否在流行文化中日益常见?当恋爱综艺节目请李松蔚分析亲密关系,公共媒体找崔庆龙剖析时代焦虑,诸如“Know Yourself”“简单心理”等公众号内容日益受到欢迎,我们是如何理解好的关系的?原生家庭对我们有何影响?焦虑问题是否真的可能被解决?
每一个夜晚,当我们点开直击生命困惑的标题,在浅显化的心理概念里寻找关于自身情绪、关系与生命的答案,心理学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的解药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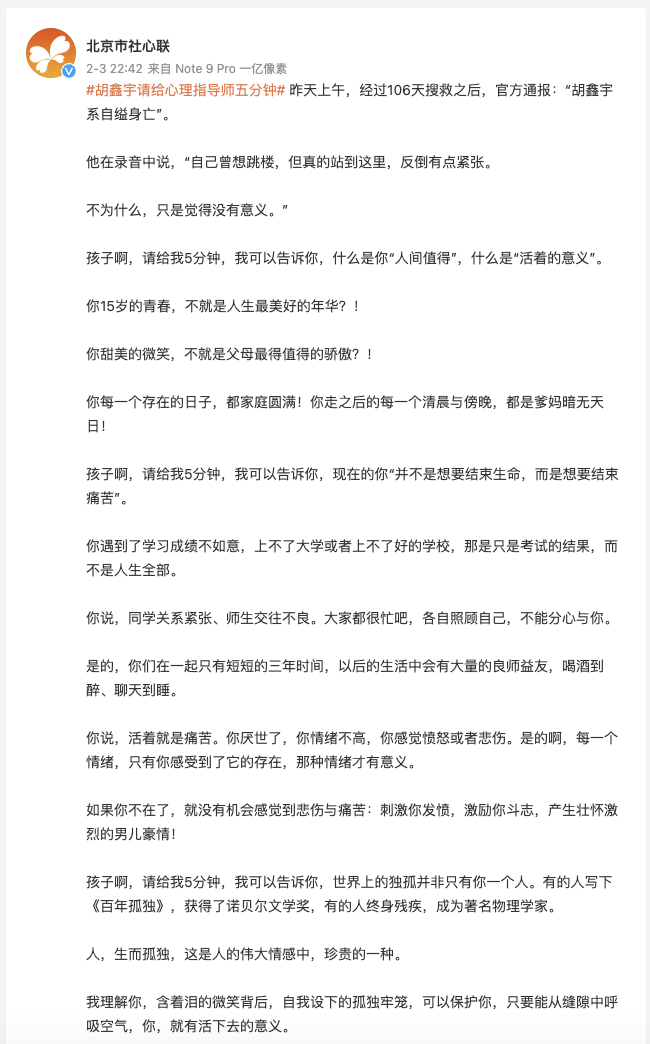
潘文捷:大学时,我是班上的心理委员。心理咨询师会找同学进行谈话,我承担着邀请大家谈话的职责。至今没有想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在电视剧里,心理咨询师和咨询者说的话、心理测试结果都是绝对私人的,绝对不可以对外人说的。可是在实际的校园生活中,如果你被判定有不妥的倾向,你的辅导员甚至你完全不认识的校领导可能都会知道。
在2011年《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压力大且抑郁,韩国人还是不愿意接受心理治疗》的文章里,朝鲜大学教授、心理学家Kim Hyong-soo称,“如果感到抑郁,韩国人会默默忍受,等它过去,因为那些去看精神科的人会感受到一辈子的羞辱。”那些寻求心理咨询的人经常去私人诊所,甚至以现金支付,这样他们找工作的时候社保上就不会显示这些记录。
可是,私人咨询更贵,普通人只负担得起公立诊所呀——我问过一位国内名气很大的心理咨询师,他说他的价格真的太高了,他自己是不会付这个钱咨询的——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既想要接受心理咨询,又为担心不知道哪儿会泄露隐私而担惊受怕。
尹清露:我和几个朋友都尝试过心理咨询,咨询时我往往想的是“只要现在不难受了就行”,但是心理治疗需要长期干预才能起效,而我那些烦恼过两天也就烟消云散了,再加上咨询费用很贵,所以最后的结果往往都是放弃。
就像文捷说的,普通人只负担得起公立诊所,但国内某些精神科医生的水平并不理想……心理咨询这个“探寻自我”的游戏,不是穷人玩得起的。
有趣的是,张鹂在Anxious China中也分析过国内不同的心理治疗流派,比如成本比较低、以证据为基础、旨在解决当前问题的认知行为疗法,就正好契合我那时的心态(顺带一提,某些AI心理咨询App使用的也是这种疗法,不知chatGPT的逻辑与此是否相关)。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我更感兴趣、更本土化的疗法,也就是灵感来自荣格的沙盘游戏疗法,客户在沙盘上画出各种意象,从而建立起和内心状态相对应的世界,但意象与内心状态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无法解释的意义相关性。一位女学生画出红鲤鱼,据说象征着她对自由自在的渴望,高大的松树则象征扎根和稳定的心境。
意象是非常中国性的概念,位于西方心理学认识论之外,荣格本人也十分迷恋《易经》和《太乙金文》。认知疗法指向人的大脑,凡事讲究有理有据,但无法给人以更多承诺。许多人说算命和心理治疗有相似的疗效,似乎也指向了一点:心理咨询中强调因果关系的那一面有时并不太足够。
董子琪:对,荣格著有《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非常震惊。想引入另一个视角,许地山在《扶乩迷信的研究》里介绍了扶乩这一传统迷信活动的由来。扶乩一度流行于有文化的士人之间,最初是用来占卜考试的,其实这也像是一种心理咨询,来确认自己最在乎的事——考运和仕途——心理咨询是不是也总是针对一个人最在乎的事?最近去世的翻译家杨苡在她的口述自传里回顾了家中的扶乩仪式,七婶叫来生前被七叔抛弃又死去的妓女小翠,不仅沟通生死,还带点纾解宽慰的意味。
想起来,不少电影里的心理咨询还真和玄幻有点关系。最初是美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电影喜欢用,像是《第六感》里的主角是帮助“见鬼”的小男孩疏导心理问题的著名专家,《异度空间》中张国荣的角色是帮助撞邪的女孩走出心理困境的医生,后来两位心理医生都卷入了自身的存在主义危机当中。
可能在这些电影的想象中,心理咨询踩在一条晦暗不明的阴阳路上,所以疏通心理的同时也可能会触碰到神秘不可说之物。
在犯罪电影中也是一样。《无间道》里帮助梁朝伟饰演的卧底角色治疗的是一位女性心理医生,她也是剧中唯一知晓他真正身份还不在乎的外人,只有在她这里,他才能好好地睡上一觉。这大概体现了一种体谅,一种对陷于无间折磨地狱中人的宽容,这世间的事不是只有对错,世上人也不是只有好与坏,即使有人游走于刀尖边缘之上,永无重见光明的希望,还是能在这里得到短暂的休憩。心理咨询像是对无间地狱的一次打断,我还挺喜欢这种处理的。
潘文捷:既然今天大家都很焦虑,寻求内心平静可以说是人们由衷的渴望。我见过许多人去寻求宗教解脱,但无神论者可能就只能寻求心理学。有需求就有商机。我曾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喻丰探讨过心理学庸俗化的话题。他说,社会人士引用的一些东西其实有一定的来源。比如“正念”这个概念特别火,这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研究点,正念时人会进入一种意识相对集中的状态,会心跳减速,感到平静,民间有很多人把它和一些离奇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认为喝茶、喝咖啡或听讲佛法都能正念。
但实际上,学者和大众在说同一个概念的时候指的不是一回事,对于学者来说,引入概念是需要做实验的,是需要经过科学检验的。
有趣的是,喻丰虽然研究的是积极心理学,但其底色有一些悲观。他告诉我,心理学不像社会学、政治学那样进行宏观的思考,是一门微观学科,指的是“在你不能宏观地做什么的时候,对自己做些积极性的事情,调试看待自己的方式”。
尹清露:流行的心理学的确有庸俗化和积极化的一面,比如开心比痛苦要好,比如“有问题就一定有原生家庭之类的原因”,再比如对美好生活的承诺被寄予在个人之上,这和人类学家冯珠娣在《万物·生命 : 当代北京的养生》中提到养生符合国家呼吁的医疗私有化、个人要对健康负责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我现在也会看到,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原生家庭并不是全部的病因”,心理咨询也不能以一举之力解决结构性问题。那么,在这时候,心理学还可以做什么呢?也就是说,非庸俗化的心理学是怎样的?我比较好奇这一点。
前阵子被一个朋友按头安利了李松蔚的新书《5%的改变》,大概是说人只能通过这副极其有限的躯体来做出行动,实现哪怕只有5%的改变,哪怕中间会有反复和退缩。我觉得这种心态也是一种可取的积极,也是普通人能够学习的心态,而不是一种“希望心理咨询能带给自己幸福承诺”的虚假积极。
林子人:喻丰说心理学是“微观学科”,有意思的是,之前《静寂工人》作者魏明毅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也提到,她做了多年的心理咨询工作,发现这个学科已经难以让自己产生满足感——无论多么努力地工作,咨询室门外等待的人依然还是那么多,苦难似乎没有消减。她因此对世界产生了很多疑惑,并且意识到这种疑惑是心理学无法解答的。在她看来,心理咨询的领域是实验性的,和真实的生命世界联系没有那么紧密,相比之下,人类学或许能给她的疑惑提供更清楚和全貌的答案。
上周读《三十不立》,这本书介绍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日本社会现象,就是三十多岁的日本青年(他们多为就业冰河期的受害者)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重大挫折,却依然咬紧牙关既不愿向亲友寻求帮助,也拒绝NGO的援手,甚至为此孤独死。
NHK现代特写节目录制组从一起孤独死事件着手调查,试图弄明白这个现象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宣扬的“自我责任论”已深深地镌刻在这一代日本年轻人的心里,这让他们耻于承认自己失败和需要外界的帮助,因为一切都源自自己“不够努力”,失败是自己应得的。此种新自由主义心理结构的形成与一种潜意识中的无望和恐惧有关:人们对撼动体制已不抱希望,只能通过改变自己适应外部环境。
虽然中国称不上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社会,但这种“自我责任论”的逻辑我们也非常熟悉,《胡鑫宇,请给心理指导师五分钟》让我们反感,正是因为我们某种程度上觉察到了“自我责任论”的限度。越努力不一定会越幸运,有些痛苦是难以用积极心态抹去的,不必苛责自己。我想,有时候这样简单的一种共情,可能反而比专业的心理咨询更能安慰人。
- 本文固定链接: https://www.douyinkuaishou.cc/?id=54309
- 转载请注明: admin 于 抖音快手 发表
《本文》有 0 条评论